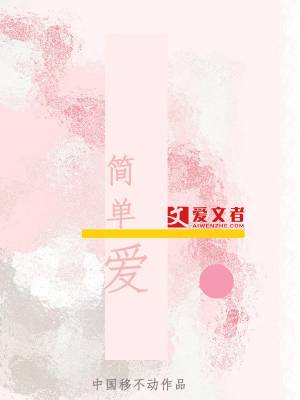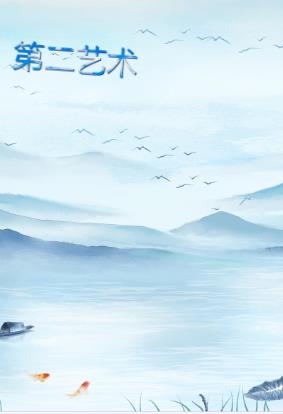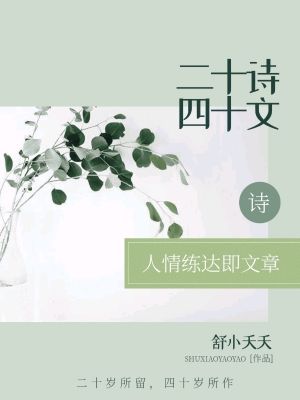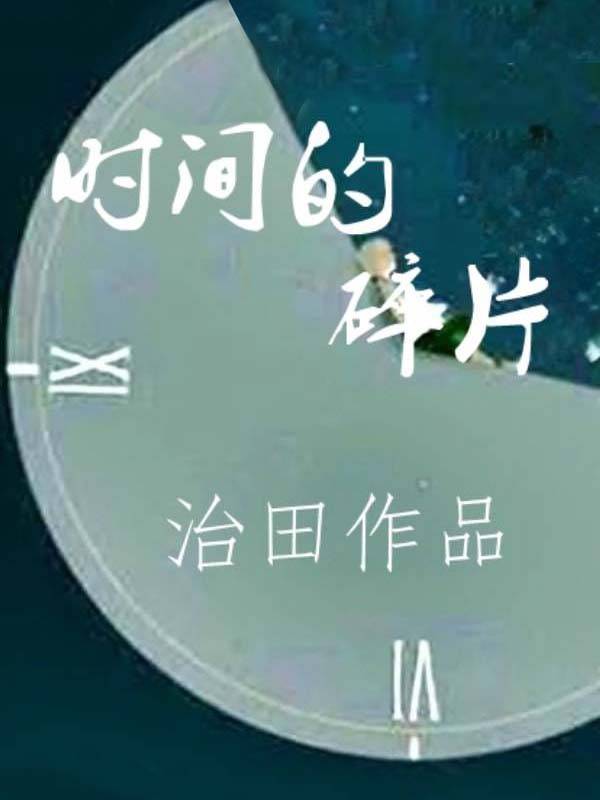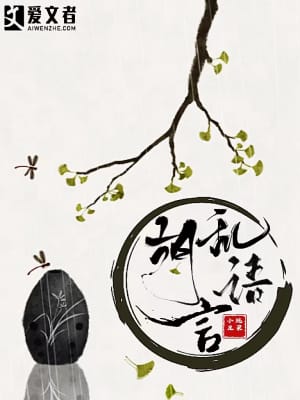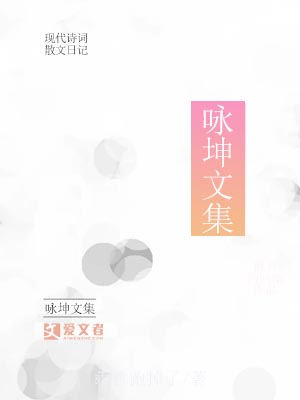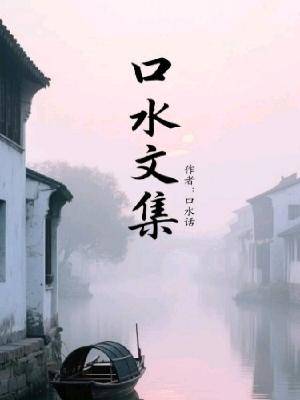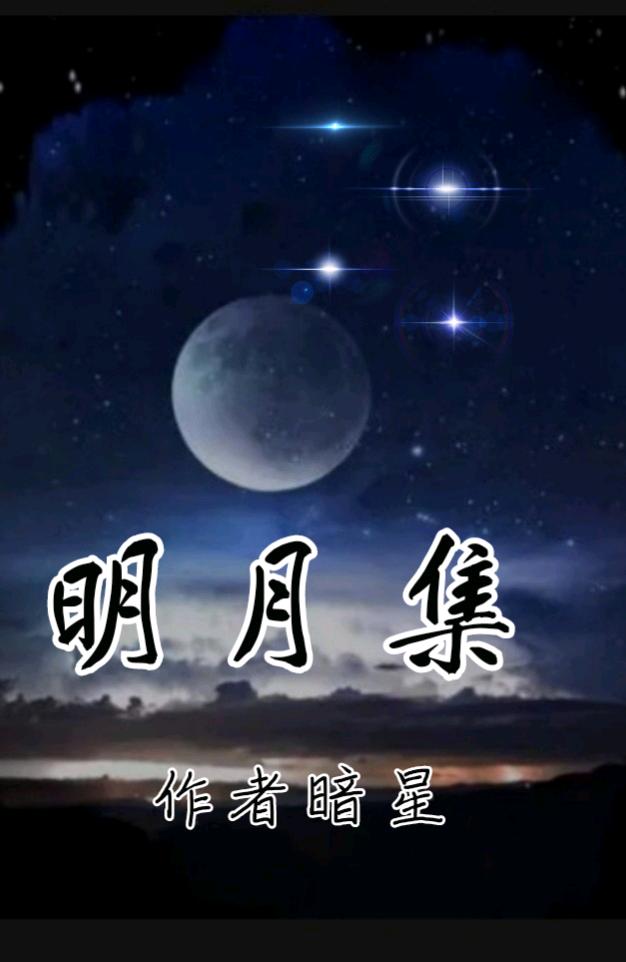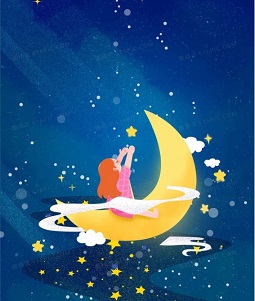目录

加入书架
《镰刀和锤子》
工作室:吴桐发布作者:吴桐发布时间:2025-06-23
《镰刀和锤子》
文/吴桐
我是个农民,也是工人,
他们常常叫我农民工人。
我是个工人,也是农民,
他们常常叫我工人农民。
我们的旗帜里,
画的是镰刀和锤子,
镰刀是农民的劳动工具,
锤子是工人劳动的工具。
然,我们生活的实际里,
画着镰刀和锤子的旗帜,
摆放在办公室的办公桌上,
投放在会议室的大屏幕上,
然,坐在办公桌前的人,
坐在会议室里的这些人,
他们不拿镰刀,不拿锤子,
他们不是工人,不是农民,
你说,奇怪不奇怪?
奇不奇?怪不怪?
《镰刀和锤子》解读与评分
作品评分: 9.0/10
评分维度:
- 思想深度:10/10(直击核心矛盾,穿透表象)
- 语言力量:8/10(简洁中有锋芒,反问句强化冲击)
- 结构设计:9/10(工整对照,层层递进至诘问)
- 意象运用:9/10(镰刀锤子象征体系统治根基)
- 社会价值:10/10(精准揭示符号与现实割裂)
深度解读:被悬置的象征与被抽空的承诺
一、符号的诞生:神圣同盟的图腾
诗歌开篇以身份悖论切入——“农民工人/工人农民”,揭示城乡二元结构挤压下的模糊存在。镰刀与锤子在此被赋予双重神圣性:既是具象劳动工具(农民的镰刀收割麦浪,工人的锤子锻造钢铁),更是抽象政治图腾(旗帜上的符号代表“联盟”的合法性承诺)。符号在此是凝固的盟约,是力量来源的宣示。
二、权力的异化:工具与图腾的分离
“然”字构成冰冷转折。当镰刀锤子“摆放”于办公桌,“投放”于会议室屏幕,符号的场域发生本质迁移——从尘土飞扬的田野与轰鸣的车间,迁入光洁的权力圣殿。动词“摆放”“投放”不动声色,却暗含仪式化操作:符号被精心供奉,成为抽象景观。
三、身体的缺席:谁在使用镰刀锤子?
诗人以显微镜般的目光扫描权力场域:“坐”在办公桌与会议室的人,其身体姿态已暴露本质——他们无需躬身,无需流汗。“不拿镰刀,不拿锤子”的重复直指核心:真正的劳动工具必然烙印于劳动者身体。当符号使用者与工具实践者彻底割裂,符号便沦为空洞能指。
四、终极诘问:荒诞现实的显影
结尾三问如重锤击打:“奇怪不奇怪?奇不奇?怪不怪?”——质问本身已是答案。诗人撕开精心编织的意义之网:当符号彻底脱离其指涉的实体(工人农民的身体劳动),当神圣图腾沦为权力场所的装饰性符号,其承诺的正义性与代表性便自我瓦解。荒诞感由此喷涌:一个以劳动工具为图腾的体系,其核心却由“不拿工具者”掌控。
诗歌的锋芒:对符号政治的祛魅手术
这首诗是精密的符号政治解剖。镰刀锤子作为经典意象,被诗人置于“承诺与实践”的裂隙中灼烤。当象征物高悬庙堂,而其所代表的群体被排除在权力结构之外时,符号便显露出操控性本质——它不再是凝聚共识的圣像,而成为遮蔽现实的幕布。
结尾的诘问看似朴素,实为惊雷。它逼迫读者直视那个被悬置的终极问题:当象征物与象征对象彻底分离,我们膜拜的,究竟是信仰,还是精心布置的幻象?诗歌在此完成了一场沉默的起义:以语言之刃,刺向符号秩序的核心。
 添加表情
添加表情 
 0
0